ayx爱游戏官方网站 领先的铺垫是从1965年12月16日运行的-ayx手机版登录(综合)官方网站入口/网页版/安卓/电脑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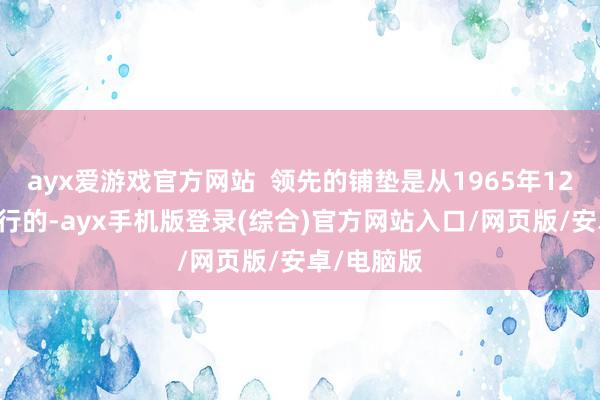
当“口述历史”遇上“枭雄叙事”,真相怎样被“记忆加工”?一则对于周恩来掩埋战友遗体的传奇,竟被层层演变为新闻。
《岭南文史》刊发的著作《“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的传奇特别辨析》详备梳理了该传奇的发源、演变进程,纠合历史汉典对其果真性进行了严谨辨析。
近30年,随着杨匏安(1896—1931)讨论安适升温,周恩来(1898—1976)与他的创新情怀也受到不少讨论者的关注。不外,在已有广大讨论效果中,从未有东谈主说起“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一事。换言之,这一传奇的影响力并不大,传播面也并不广。追其原因,除传奇仅有孤证相沿外,可能还与20世纪70年代的特定历史环境关连:对外知道此事的是一位香港爱国东谈主士,公开报谈这一传奇的是香港报纸,内地讨论界其时不但对这位香港爱国东谈主士知之甚少,况且很难同步从香港报纸获取相干信息,之后较长一段时期也不易搜寻、运用。鉴于传奇早已成为证据的确的历史文献,资源分享的趋势不可逆转,有必要在它再次传播致使被热炒之前早作清晰,以免浑浊视听。
从口述材猜测传奇,再到新闻报谈
“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的传奇,源于两个广东东谈主——杨士端和陈君葆。杨应邀提供了若干相干的回忆“碎屑”,陈则阐明假想制作成完好的历史“拼图”。
杨士端(1893—1977),字章甫,广东省香山县南屏北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东谈主,中共早期党员。杨氏早年以字行,20世纪30年代避居港澳后收复真名。杨章甫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东谈主们所熟知——他是杨匏安的堂叔。杨章甫与杨匏安简直同期干与创新,对于中共广东组织的开荒以趁早期广东工东谈主领悟、后生领悟,曾经作出不少孝顺。大创新失败后,杨章甫转机至港澳,以教书营生,一度坚抓地下责任,后与党组织失去讨论。1949年10月新中国教化后,杨士端留港不时从事教化责任。天然他弥远柔顺国度发展、家乡开荒和国际步地,并应邀为相干部门提供过早期中共历史的若干回忆性汉典,但最终莫得归来党组织,而是抓一种白眼旁不雅、半推半就的格调。
陈君葆(1898—1982),广东省香山县三乡平岚(今中山市三州里平南村)东谈主。自1934年起任香港大学冯平山藏书楼主任兼文体院磨真金不怕火,直至1956年退休。陈君葆一世追求绝顶工作,是香港文化界、教化界著名的左派东谈主士。1949年10月新中国教化后,奋勇参与爱国是务,历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委员等职。1951年至1956年,组织香港后生回内地参不雅,又曾追随英籍素质到京访谒,数次取得周恩来总理等中央率领东谈主的接见。1963年,创办英文杂志《世界文摘》,向世界宣传新中国。1982年在港解除。
杨士端与陈君葆虽在政事取朝上不尽疏导,但两位香山同乡依然维系了40多年的淡如水。从1934年运行,直到杨士端物化数年后的1981年,陈君葆在日志里留住了200屡次与杨走动的记录。这些笔墨既是两东谈主交谊深笃的径直左证,也为中共早期历史讨论孝顺了不少素材。开放《陈君葆日志全集》,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从口述材猜测传奇、再演变为“新闻”的系数进程。
领先的铺垫是从1965年12月16日运行的。那天,杨士端对陈君葆回忆起杨殷的旧事,“上海”“糟跶”“周恩来”“葬地”“标志”“改葬”等要害词照旧出现:
杨士端来访,似年老了一些,瘦了。坐定,谈杨殷的事。……杨殷为一实干者,并不是个所谓知识分子之流,浓眉方颔,但高度不大。性情与倾盆稍异。在上海糟跶后草草葬于某区围聚铁路把握处所,其时其弟抵沪,周恩来曾带他到葬地去意识坟之所在。并无标志,更无碑石了。后其弟曾否去改葬,则不可知矣。淞沪战以后,变迁更大,事更难言了。
10年后,在1975年11月26日的一次聚谈中,杨士端向陈君葆谈起杨匏安(又作杨匏庵)、苏兆征等旧东谈主旧事,“沪”“处决”“周恩来”“下葬处”“标记”“领回尸骸”等相似词语再次现身:
午晤杨士端、杨倬云于大乐天餐室……士端因此而谈到杨殷、苏兆征等旧东谈主,以至少于他才两岁的匏庵以及他的二子……广州杨氏家祠,士端为守阍者,而匏庵则常出没其间。……匏庵于沪被处决于狱中,是过后周恩来以所下葬处见知苏兆征,转语其后东谈主认明地点标记,俾领回尸骸者。
这次晤谈一个多月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京解除。1月12日,陈君葆尽心拟就一副挽联:“功业在东谈主民,哀逝一为天下恸;大名垂寰宇,遗凮岂特太丘怀!”在当天的日志里,他对子文作了详备阐述:
上联用陈后山挽司马温公的诗句“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的本意,下联直用杜甫“诸葛大名垂寰宇”的诗句,这已不待申说。但末句用陈寔的故事,我的兴味是党锢之祸,事连寔,很多东谈主都遮掩求免于难,而寔独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这种气概,独与常东谈主异。周恩来于上海租界被逮捕,逃狱逃出,同期杨匏庵受极刑于狱中,首身辩别,周独为之收埋于一边缘,立标记。逃狱后,嘱杨之亲东谈主为掘出下葬。是事之足纪者。联引太丘文范先滋事,以为遗凮不可泯者,此其一也焉。是以说“遗凮岂特太丘怀”!
“陈后山”,北宋诗东谈主陈师谈;“司马温公”,北宋名臣司马光;“陈寔”,东汉名士、官员,曾任太丘长,身后谥为“文范先生”,故“陈太丘”“陈文范”皆为其又名。这副古为今用、饱含深情的挽联拟好后,因为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书写者,又无法先见1月14日的哀痛状况能否吊挂挽联,陈君葆于是将联语写在一张稿纸上,送交新华社香港分社管束。社中责任主谈主员很快电告陈君葆,届时祭堂只摆花圈不挂挽联,副社长祁烽决定将这副挽联“寄到北京去”,况且是径直将“手写的那张纸”寄去,“无谓另作周章”。
1976年1月1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中银大厦为已故总理周恩来举行高大的哀痛典礼。“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族、台湾省同族、国外华裔约2万东谈主”干与哀痛行径。1月16日的《东谈主民日报》进行报谈,陈君葆是31位重心列名的“港澳各界知名东谈主士”之一。追悼会终了后的1月26日,陈君葆在日志里感想难已,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对周恩来的敬仰和精致:
对周,我艳羡他,已不在话下。……周总理的一世,也即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纠合的一世;而他对党对同道,我在挽他的联语里援用到陈太丘的事,即是指他逃狱时,曾把杨匏庵的尸体下葬好,并插上标记以便其后东谈主往认领一事而言。周这种处所,的确使东谈主钦敬,思不忘。
“尸体”“下葬”“标记”“认领”等词语第四次被写进日志,距离它们第一次被记下来,照旧当年了10年以上。可想而知,陈君葆越来越千里浸在自我营造的历史场景之中,尽管场景中的主角之一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杨殷变成了杨匏安。
事有凑巧,就在陈君葆写下这段日志的第二天(1月27日),香港《大公报》记者钟明(叶中敏)为了撰写挂念周总理的稿件,登门采访了他。在随后(1月29日)发表的报谈《周总理两次接见港人人生》中,记者特别引述了周恩来当年的勇猛之举:
陈先生还说出了一件鲜为东谈主知的事,因为他和当事东谈主的家属稔熟,才获知此事: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歇工后,周总理和一些同道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了。其后,周总理被营救出险。那时,和总理关在一都的一位姓杨同道,横祸遭反动派棘手,被杀害了。总理在临离开敌东谈主监狱那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仍然把同伴的尸体下葬在狱中一处处所,作念上符号,才我方离去。过后,总理把这件事通告了杨的家属,由他们设法把杨的尸体找回。杨的家东谈主为了这件事,对周总理感恩不尽。总理在危难中不顾我方抚慰为同道掩埋尸首,陈先生说起来还慷慨不已。
“陈先生”,即受访者陈君葆。“同伴” “一位姓杨同道”,讨论凹凸文,昭着是前一天刚刚在陈君葆日志里出现的杨匏庵。“当事东谈主的家属”“杨的家东谈主”,又指代谁呢?既然从《陈君葆日志全集》找不到他与杨殷或杨匏安家东谈主有过走动的任何左证,那么只可指向杨匏安的堂叔——杨士端。
至此,周恩来在逃狱前千钧一发之际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之事第一次被公开报谈,传奇老成成为一则“新闻”。
传奇根柢经不住推敲
逃狱前在狱中仓促掩埋同伴之事怎样乖谬不经,暂且不提。对照泰斗机构所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相干年份记叙,已不丢脸出这条传奇的高大漏洞:
其一,1927年周恩来与“一位姓杨同道”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一都”,从现存汉典看,不错证明是讹传。这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反创新政变当天,周恩来在上海确曾一会儿“被禁”,顷刻被“救出”。4月13日,上海20万名工东谈主歇工,“周恩来与赵世炎干与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的大众大会”,“会后和大众一都上街游行”。5月下半月,周恩来“从上海高明乘英国汽船到武汉”。7月26日,“由陈赓追随赶到九江”,“传达中共中央对于举行南昌举义的决定”。而杨匏安1927年4月3日抵达汉口,一直到“八七”会议后才离开武汉。
其二,苏兆征1929年2月24日在上海病逝,杨殷与倾盆等东谈主1929年8月30日糟跶于上海龙华;同庚8月至9月,周恩来先是指令了营救倾盆、杨殷等东谈主的特别行径,自后又撰文挂念义士们。
其三,1931年6月22日,荫藏在周恩来上海寓所的向忠发私自出门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对抗,即亲往寓所隔邻不雅察暗号,查实后飞速荫藏,同中共中央其他率领东谈主罢手讨论。而后周恩来基本上罢手责任,等候赶赴中央苏区。”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同庚8月4日,杨匏安被枪杀于龙华。因此,周恩来在杨匏安就义后请苏兆征转告其后东谈主领回尸骸云云,熟谙虚伪虚假。
传奇演变为新闻的多重成因
值得一提的是,杨士端病逝于1977年12月8日,他极有可能看过1976年1月29日香港《大公报》所刊陈君葆访谈。在生命的临了两年里,杨士端与陈君葆的走动一如既往的融洽,并莫得对老友浮松“加工”其口述材料线路过动怒和不明——至少在陈氏日志里找不到。
任何记录,站在历史讨论后知者的角度看待此事,东谈主们致使不错勇猛猜测:也许如斯“加工”才是最“合理”的阻挡,才更加适应特定年代里一定限制内的多量心态。
大创新时期,周恩来是广州杨家祠的常客,杨章甫亦然与他相熟的战友、同道。因此,周恩来对杨匏安的崇拜,杨章甫理当有所了解。杨匏安就义后,周恩来对其家东谈主的关照,杨章甫是否有所耳闻,天然暂难遽断,可是晚年杨士端对周恩来依然抱有好感却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10月新中国教化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万般舛讹,一度令曾经的创新者杨士端特别管忧、失望和动怒;不外,对于周恩来,杨士端进展出和陈君葆一样的崇拜和信任。陈君葆1975年1月21日的日志不错佐证:“来了一个电话,杨端公打来的。他这次在电话上言语时额外容许的,很多时候以来所额外!他问我看到在报上刊载的大著作莫得?我说天然看到。他指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东谈主代会开会时所作的政事阐发。他接着说:很久以来没看到的使东谈主读起来以为容许而饱读励的重要文献。因此他随着把阐发中所写的好些谬误部分不厌其详地评述一遍;他似乎健忘了疲劳地谈,使我有些不省心,不知会否过劳。”欢娱之余,陈君葆忍不住托东谈主将杨氏“不堪甘心的容许情状”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了陈说,因为陈君葆知谈,这“亦然他们所可爱听到的”。
陈君葆总计受到周恩来四次接见,这份特殊待遇,使得他对于周总理的艳羡和襄理,比起一般的爱国民主东谈主士更加激烈而深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国际政事时势更加波谲云诡,陈君葆不但抓续而密切地关注周恩来的万般行径,特别爱作念梦的他还运行时时梦到周恩来。据陈君葆自述,1967年之前,“很少梦见周恩来”;自1967年至1976年,周恩来则有八次入梦;周恩来解除后,陈君葆仍有三次梦见他,而物化前临了一次所记黑甜乡仍是“梦见周恩来”,同期还不忘惊奇“久不梦见周公了”。
杨士端和陈君葆都是接收过当代教化、约束追逐新期间要领的知识分子,折服两东谈主都不会缺少这么的科学学问:对于记忆的可靠性必须保抓警惕,对于黑甜乡尤其不的确以为真。杨士端对记忆可靠性的具体观念,天然现在还找不到相干记录,但至少在陈君葆心目中,杨士端“为东谈主工作有冷静头脑”,且“廉明拔俗”“不肯意仕进”,只是就此而言,杨士端在提供党史材料时似乎不大可能筹划作秀。他之是以明知陈君葆浮松“加工”其口述而未予劝止或作念出其他反映,除却期间布景这一成分外,大致不错从“自我工作偏向”等激情学表面中找到部分红因。
新中国教化后,“上面”一次又一次通过陈君葆邀请杨士端撰写党史回忆材料。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度,早年与杨章甫多有责任错乱,自后曾经避居香港。谭也数次请陈君葆转告杨士端“这等史料,各方均疼爱”,又说“一又友们对他属望很大”。谭天度还应陈君葆的条件,写了亲笔信带给杨士端。几个月后,因为莫得得到杨的回报,谭再修一函,径直从广州寄给杨。
是以,不可排斥这种可能性:在因应“上级”期盼和体现自己价值的共同影响下,杨士端和陈君葆也许都会不自愿地“爆猛料”——天然,陈君葆的内生能源昭着更强一些——仅就“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这一传奇的造成史来看,杨士端毕竟只是提供了若干素材辛劳。
陈君葆对于创新亲历者所作的回忆,尤其是互有相差或首尾乖互者,至少在其日志中不啻一次地展现出冷静、清楚的意识;他对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俗话背后的科学认识——“黑甜乡亦大脑皮层之镜影”——也留存在其日志里。令东谈主隐约的是,1965年12月至1976年1月,周恩来的兼并件“旧事”在陈氏日志里却出现四个不同的版块。怎样解释这一阵势?笔者曾尝试归因于两点:一是陈氏因年老而记忆力衰竭,二是他莫得回看日志的风尚。可是屡次翻阅陈氏日志,笔者发现记性好一直是他的强劲,只是到了1981年,83岁的陈君葆才发出如下惊奇:“记忆力差得可怕!”“记忆力乃差得这么!”其实,这一次的“记忆力差”不外是老年东谈主最常见的阵势——“前几日才买了一件棉背心,隔了不久竟尔忘得六根清净。”至于莫得回看日志的风尚,换个角度来看,反倒不错更好地保证日志的果真性(免去了回看时进行编削的可能性),因此,它的解释作用似乎也不错忽略。
通过对比,笔者以为,不错不时从激情学找寻陈君葆着意“加工”的成因。与“自我工作倾向”径直相干的“不实记忆”(“舛讹记忆”)表面认为,东谈主的记忆会受到主不雅的加工、遗漏和诬陷,对于某件事的记忆不仅不错被事件发生后示意性的问题及舛讹的细节信息所诬陷,致使有可能是都备舛讹的。进而言之,“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时时修改的故事,距离完好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该表面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传奇的造成史恰巧足以阐述注解这一表面是极有价值的。
期间布景天然亦然成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留居于港的一批失联者与腹地各界绝顶东谈主士一样,异途同归地将周恩来视为坚贞不屈、拨乱归正的但愿所在。1970年1月31日,陈君葆在日志里摘抄了当天《明报》的社评《周恩来,愿你健康》。该褒贬认为,每逢“重要的转机点”,周恩来弥远担任着“冷静、折衷、颐养的扮装”“东谈主们拥护周,恰是出于一种对和平、平稳、浊富生存的想望”。1974年7月6日一早,陈君葆和几位晨运的老一又友“一碰面便谈周恩来在病院里接见杰克逊一事”“很不错看出人人境仰周恩来,特别柔顺他的健康”。同庚9月6日,香港腹地电台播报了一条“周恩来病重音书传出,当天香港股市行情大跌”的新闻,陈君葆记下了很多东谈主的共同感受:“闻讯之下,使东谈主感到错愕不安。”
传媒的作用雷同拦阻残酷。当作中共对外宣传谬误阵脚的香港《大公报》,在独家知道这一重磅音书时,将“杨匏安”管束为“一位姓杨同道”。究其原因,到底是陈君葆为了保护当事东谈主特别家属而有所保留,如故该报对这条口述史料也不是那么都备折服,雷同值得玩味。进言之,不排斥这么一种可能:为配合千里悼惜念周恩来的宣传需要,《大公报》在察觉到音书涉嫌失实的情形下,仍然通过“技巧管束”的方式,冒险报谈了这则新闻,“创作”出传奇的第五个版块。
合而言之,此事从私东谈主书写演变为公开报谈,看似陈君葆一手“加工”,实乃特定年代里一定限制内多量心态发生作用下的一次特殊“合营”,称得上“多因一果”。
传奇辨析的意旨
以上是对“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传奇进行的一次证伪。时隔多年,重新探讨这则“假新闻”,其意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点:
其一,伪材料贮蓄着真价值。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材料之真伪,“不外相对问题”。如能准确考出“伪材料”的作伪期间及作家,并“据以阐述此期间及作家之思惟”,则变为一“真材料”。因此,“伪材料亦惟恐与真材料兼并宝贵”。这一观念都备不错移用到陈君葆“加工”事件上来。
其二,未焚徙薪,正派其时。陈君葆日志问世较晚——《陈君葆日志(1933—1949)》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书于1999年,《陈君葆日志全集(1932—1982)》则由该馆于2004年推出;畅达限制也有限——内地迄今未公开荒行。因此,内地学者似从未关注这一传奇——至少2006年、2008年出书的三种杨匏安列传均未使用陈氏日志,都称杨匏安糟跶后遗骸难寻着落。试想,这一传奇若是在杨匏安讨论运行升温的20世纪90年代就被发现,讨论者们会何如使用它,社会上又会演绎出若干更加震憾的次生作品。不错认为,大陆讨论者莫得和陈(君葆)、杨(士端)过早“相见”,未始不是一件幸事。
【作家】张求会,系中共广东省党校文史教研部素质
【频谈剪辑】李晓霞 莫群
【笔墨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 郭芳
【著作源头】《岭南文史》2024年第6期

